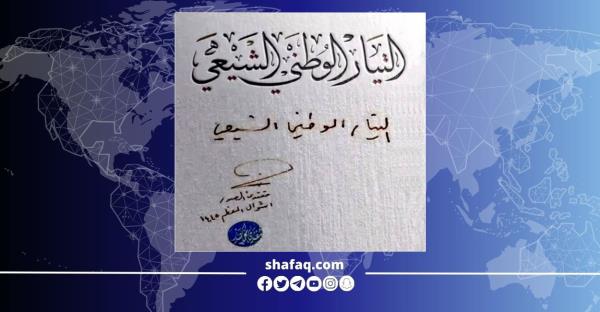密封质量评价不仅在石油系统研究中至关重要,而且在地下储氢等其他地质体应用中也很重要。在没有断层或其他不连续性的情况下,毛细管突破压力控制着顶部密封能力。在缺乏实测毛管压力数据(如岩心)的盆地中,区域压实-孔隙度趋势可以作为估计泥岩毛管性质的首选预测工具。存在数学压实模型,但需要针对每个盆地进行校准。建立了基于理论模型的压实趋势,并与实测毛管压力曲线推断的理论最大油气柱高度进行了比较。采用x射线衍射仪、Eltra C/S分析仪和岩石热解法对维也纳盆地中新统中上段泥岩岩心样品进行了研究,测定了样品的总体矿物学、总有机碳和游离烃含量。应用宽离子束扫描电镜、压汞毛细管孔隙度测定法和氦密度测定法获得了维也纳盆地孔隙结构特征,并将数学压实模型与实际孔隙度数据进行了比较。孔隙度深度递减趋势明显,表明维也纳盆地中部机械压实作用较为均匀。将维也纳盆地趋势与全球泥岩压实趋势进行比较,推断出区域隆升导致了高达500 m的中新世上部地层的侵蚀。岩石评价参数S1和生产指数[PI=S1/(S1 + S2)]随研究泥岩毛管封闭能力的减小而增大的趋势可能表明油气通过低渗透泥岩层向垂向运移。这一观察结果必须在未来维也纳盆地二次储存应用的顶封研究中加以考虑。
维也纳盆地从奥地利延伸到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图1a)。中新世盆地填充物厚度最大可达5 km以上(图1b),其上覆各种基底单元,包括从基底到顶部结晶基底、原生中生代沉积、新生代前陆盆地沉积和阿尔卑斯推覆体(弗理石带、钙质阿尔卑斯;Wessely 1988;arzmller et al. 2006)。在中新世(Ottnangian - Pannonian)盆地充填层和基底单元中发现油气,使维也纳盆地成为中欧主要的油气省之一。迄今为止,已发现160个油田,累计可采储量约为1.60亿桶油当量(Boote et al. 2018)。
图1

a维也纳盆地在中欧的位置;黑色矩形表示(b)。b维也纳盆地取样井在构造和区域地质图中的位置[根据Rupprecht et al.(2018)修改]。c研究了维也纳盆地的岩心样本(68),根据深度排列。请注意,样品根据(b)中所示的井位进行了颜色编码。斯坦伯格的错
由于广泛的油气勘探,人们对维也纳盆地的构造和演化及其含油气系统有了普遍的了解(Wessely 1988;arzm
ller等人,2006;Rupprecht et al. 2018)。然而,关于年轻人(后潘诺尼亚;< 9 Ma)盆地隆升史。尽管对烃源岩和储集岩的分布和质量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但由于大量明显保存的油气聚集,对密封岩质量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然而,由于可靠的盆地运移历史模型可能会带来新的发现和更长的生产寿命,近年来,封底质量越来越成为成功的因素。此外,与顶封相关的问题与二次储存安全(如CH4, CO2, H2)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理论上定义水湿密封静态顶部密封能力的参数是毛细管进入或突破压力,因为它限制了储层结构可能容纳的浮力流体的最大数量(Schowalter 1979)。在这种纯顶部密封控制的情况下(不包括圈闭几何形状或充注等其他因素),整个流体柱的密度驱动浮力压力加上可选的额外水动压力分量(例如,由于下伏地层的超压)必须通过作用于密封岩石中的毛细力来平衡。因此,评估,特别是大型结构的评估,应始终包括基于阈值突破压力估计的最大流体柱高度的计算。
在没有岩心材料的情况下,泥岩的封闭能力基本上是给定流体体系的孔喉分布的函数,可以根据假设的“正常压实趋势”来估计。对于不同的盆地和压实机制,已经建立了这种孔隙度/深度关系(Athy 1930;Hedberg 1936;韦勒1959;米德1966;Sclater and Christie 1980;Baldwin et al. 1985;Yang and Aplin 2004;Mondol et al. 2007)。然而,这些正常的压实趋势只能提供一个粗略的估计,可能过于简化,不能代表单个盆地尺度的情况。孔隙压力条件、矿物学组成、颗粒大小和结构的变化或成岩过程等许多因素都对盆地内细粒沉积物的压实行为产生强烈影响(Bj?rlykke和H?eg 1997;Bj?rlykke 1998,1999,2014;Mondol et al. 2007;Fawad et al. 2010;德鲁斯等人,2018)。因此,这项工作旨在测试理论压实趋势模型在维也纳盆地实际岩石物理孔隙度和毛管压力数据预测中的一般适用性。为此,采用x射线衍射、He-pycnometry、压汞毛细管孔隙学、宽离子束扫描电镜以及岩石热解分析等方法,对维也纳盆地中覆盖深度700 ~ 3400 m的68组中第三系(潘诺尼亚、萨尔马提亚和巴登尼亚)封岩进行了详细研究(图1c)。从特征良好的泥岩层段中获得的区域孔隙度-深度趋势与模拟的正常压实趋势的比较,将有助于未来对一般压实和由此产生的密封能力模型进行校准(Yang和Aplin 1998,2004,2007和2010)。此外,还介绍了岩石热解法在低渗透泥岩中游离烃探测中的应用,作为一种潜在的地球化学工具来揭示油气垂向运移。除了顶封评价外,探测到的孔隙度-深度趋势也将用于阐明盆地后潘诺尼亚期的侵蚀历史。
维也纳盆地地区的沉积序列被细分为三个构造地层单元(Wessely 1988)。原生单元由侏罗纪至白垩纪同裂谷及后裂谷沉积和古近纪糖蜜沉积组成。异地单元由阿尔卑斯-喀尔巴阡推覆复合体(包括弗理石带和钙质阿尔卑斯)组成,在晚渐新世和中新世早期逆冲了本地单元(Beidinger and Decker 2014)。
维也纳盆地中新世充填形成了最上层的构造地层单元。中新世沉积开始于早中新世(ottnangan - karpatian)盆地演化的背上阶段(Steininger et al. 1986;塞弗特1996;Wessely 2000)。经过一个构造阶段,引起了下中新世沉积物的强烈倾斜和侵蚀,在拉分和伸展构造控制下的盆地中,沉积在中新世中晚期继续进行。中新世中期沉积速率较高且相当均匀(0.9-1.1 m/kyr),但中新世晚期沉积速率通常较低(0.4-0.9 m/kyr) (H?lzel et al. 2008;Lee and Wagreich 2017;Harzhauser et al. 2019, 2022)。中新世盆地的构造主要由两个超过5公里深的洼地控制,它们被“中央高地”分隔开(如Matzen高地,图1b)。坳陷向西与垂直位移达6000米的主要断裂带接壤(Steinberg断层;图1 b)。东(南)缘沉积中心的断层不太突出。中新统中上统沉积物的构型受5个三级层序(Ba1 ~ Ba3;Sa1;Pa1),可与Haq et al.(1988)和Hardenbol et al.(1999)的全球三阶海平面旋回相联系。
巴登期(~ 16-12.7 Ma,图2)演替(巴登群)包括三个沉积旋回(Ba1 ~ Ba3) (Harzhauser et al. 2020;Siedl et al. 2020):
(i)
下巴登纪(Ba1)沉积物包括下部的辫状河沉积(Rothneusiedl Fm.)和上部的海相三角洲沉积(Mannsdorf Fm.);
(2)
中巴登统层序Ba2下部为海侵砂岩(Matzen组),上覆开阔海相粘土和泥灰岩,上覆粉砂和细砂夹层(Baden组)。在边缘地区,巴登组与珊瑚科灰岩(Leitha Fm.;Riegl and Piller 2000)。Ba2旋回的最大淹没面代表了盆地最广泛的洪水事件(Siedl et al. 2020)。水深约为250米(Hohenegger et al. 2008;Kranner et al. 2021)
(3)
上巴登纪层序Ba3是在Langhian/Serravallian边界海平面下降引起的侵蚀事件之后形成的(Piller et al. 2022)。在Ba3沉积期间,地形高点被淹没,最后的完全海相三角洲体系沉积(Rabensburg Fm.;Harzhauser et al. 2020;Siedl et al. 2020)。在拉本斯堡地层的基底部分发现了薄硬石膏层。(Harzhauser et al. 2018)。
图2

岩石地层单元与标准年代地层阶段的地层图[继Harzhauser and Piller (2004a), Gradstein et al. (2020), Harzhauser et al. (2020)]
萨尔马提亚层序(~ 12.7 ~ 11.6 Ma,图2)厚度达1000 m,为三级层序Sa1 (Harzhauser and Piller 2004b)。它包括下部的Holíc组,由灰色钙质粘土、粉砂岩和罕见的酸性凝灰岩层组成(Harzhauser和Piller 2004a)和上部的Skalica组。后者包含泥灰岩和粉砂质砂岩以及砾岩,包括混合的硅-塑-钙质沉积物,如鲕粒、造岩coquinas和有孔虫生物构造(elesamuko和Vass 2001)。萨尔马提亚海的平均水深估计在50米左右(Kranner et al. 2021)。
潘诺尼期(~ 11.6-7.2 Ma,图2)的特征是潘诺尼湖从维也纳盆地扩张并最终退缩(Magyar et al. 1999)。潘诺尼世演替包括厚达1200米的陆源沉积和陆相沉积(Harzhauser et al. 2004)。下至中班诺世演替以湖相泥灰岩(Bzenec Fm.)和古多瑙河三角洲裂片(Hollabrunn-Mistelbach Fm.)为特征(Harzhauser et al. 2022)。上潘诺夫期段以陆源湿地环境为主,其特征是基底部分(?áry Fm.)的褐煤煤层和上部(gely Fm.)的砂泥相(Harzhauser and Tempfer 2004;Harzhauser et al. 2004)。上潘诺尼亚期的沉积物大面积缺失,这可能表明维也纳盆地的大部分地区在潘诺尼亚期后受到了约400米的侵蚀(Harzhauser et al. 2022)。
维也纳盆地的油气系统主要来源于本生单元的上侏罗统Mikulov组(Ladwein 1988;Ger?lová et al. 2015;Rupprecht et al. 2017)。储层存在于所有三个构造地层单元中,但与本研究最相关的是在中新世盆地充填的海侵和退积砂岩中发现的大量储层。在Matzen油田,油气产自中新世下9层、中新世中25层和中新世上4层(arzmller et al. 2006)。中新世下储层砂通常是由页岩隔离的盆地或三角洲平原的细长透镜状体。中中新世储层沉积于海侵岸线环境(Matzen Fm.)、三角洲前缘和三角洲斜坡环境,浊积岩储层砂岩较为少见。上中新世(潘盆世)储层砂沉积于三角洲-平原和三角洲前缘环境。萨尔马提亚和潘诺尼亚储层通常含有大量天然气和少量石油。封印岩的代表是在最大洪水事件期间沉积的厚包细粒碎屑岩,或覆盖单个三角洲裂片的泥岩。
盆地奥地利部分的油气圈闭与主要断裂(如Steinberg断裂)、包括前新近纪底(Aderklaa和Matzen)在内的中央高点以及南部和东南部断裂系统(arzmller et al. 2006)有关。钙质阿尔卑斯山脉存在潜山和逆冲圈闭。
生烃主要发生在逆冲和中新世盆地沉降期间。由于维也纳盆地油气系统位于成熟烃源岩的正上方,且存在较大的垂直断裂和大量的垂直堆叠储层,因此维也纳盆地油气系统被归类为垂直排水。过去,人们认为水库充注主要发生在主要断层上(Ladwein 1988;arzmller et al. 2006)。然而,油气生成和运移的时间表明,第二次运移过程可能直接通过半渗透泥岩密封层(Misch et al. 2021)。
该研究基于维也纳盆地沿30公里长的NE-SW剖面剖面大致排列的24口井的68个岩心样本(图1b)。这些取样的岩心来自部分于20世纪70年代钻探的油井,因此已经在空气中储存了几十年。Bensing等人(已出版)对维也纳盆地潘诺尼亚演替中保存的新旧岩心材料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测试存储的岩心材料对孔隙结构研究的适用性。用多种孔隙度测定技术测定的泥岩孔隙度与来自相同深度和地层的储存岩心和新鲜岩心具有可比性,这证实了储存岩心在孔隙度-压实研究中的适用性。所调查的样品为中新世钙质泥岩(潘诺尼期11个,萨尔马提亚期13个,巴登期44个),覆盖深度为720 - 3270 m(图1c)。所有样品都取自几米厚的泥岩层,以捕捉纯泥岩压实过程,而不是混合岩性的影响。因此,没有考虑其他岩性,如莱萨石灰石或巴登尼亚中期的蒸发岩。井位为Hohenau、Dobermannsdorf、Zistersdorf、Spannberg、Bockfliess和Aderklaa。通过x射线衍射(XRD)、岩石评价参数和宽离子束扫描电镜(BIB-SEM)对所有样品进行了体矿物学测量,同时对41个样品进行了压汞毛细管孔隙度测定(MICP)和He-pycnometry测量。
x射线衍射,BIB-SEM, Eltra和岩石评估测量在Montanuniversit?t Leoben石油地质主席的实验室进行。在Friedrich-Alexander University erlangen - n
rnberg岩石物理实验室进行了压汞毛细管孔隙测定(MICP)和He-pycnometry实验。
x射线衍射
使用Panalytical X 'Pert3粉末衍射仪对无纹理粉末样品进行了XRD的大量矿物学研究。将样品手工磨成约10 μm的晶粒尺寸。测量采用cuk α-辐射(11.54 ?, 45 kV, 40 mA),矿物定量采用Schultz(1964)的方法。测角仪转速设置为0.5°2θ/分钟,配准范围为2 ~ 66°2θ。定量的矿物相包括石英、斜长石、钾长石、方解石、白云石、黄铁矿、菱铁矿和块状粘土矿物。
氦比重瓶测定法
采用Micromeritics AccuPyc II 1345和氦气测定所选样品的骨胳密度(ρs)。样品重量和体积范围从5.38-20.88 g到1.97-7.63 cm3。利用MICP测量的体积密度(ρb)计算孔隙度值ΦHe (Hedenblad 1997;Krus et al. 1997)
(1)
压汞毛细管孔隙度法
MICP测量使用了Quantachrome Poremaster 60仪器。该机器产生的压力高达~ 400mpa (6000psi)。样品质量为1.69 ~ 2.66 g,体积为0.71 ~ 1.08 cm3。样品材料在105°C下烘干12小时后进行分析。为了获得可靠的孔喉半径和孔隙度值,假设孔喉分布的不规则形状部分不能反映真实的进入压力(Busch and Amann-Hildenbrand 2013)(图3),通过手动挑选进入压力来校正毛管压力曲线的表面粗糙度。挑选的进入压力范围为0.24至0.52 MPa。然后,对每条修正曲线的拐点进行切线拟合,得到位移压力和相应的位移孔喉半径。
图3

用于表面粗糙度校正的典型hg注入曲线示例(样品62_SPA8_1380)。(a)中的虚线从总曲线中移除,通过手动选择进入压力,因为它被解释为填充样品表面的不规则性(Amann-Hildenbrand et al. 2013)。注意需要纠正的部分形状不规则,下面部分轮廓光滑。b对注入曲线拐点(pp)拟合切线,得到位移压力(pd)。
宽离子束扫描电子显微镜(BIB-SEM)
用于BIB-SEM研究的样品用Buehler IsoMet低速精密刀具切割,以尽量减少机械解体。水被用作冷却剂/润滑剂。
bib抛光使用日立ArBlade 5000系统(铣削能量为8千伏,3小时)。然后使用Cressington溅射涂布机108auto(溅射时间30 s)将样品涂上金。
扫描电镜图像采集使用TESCAN CLARA场发射(FE)显微镜,安装TESCAN Essence image Snapper软件(版本1.0.8.0)。图像在10千伏电子能量下拍摄。每个样品的制图程序包括(i)一张~ 1000 × 1000μm和4000倍放大率的大面积地图(C1),以及(ii)三张~ 200 × 200μm和20000倍放大率的详细地图(C2-4),对应的像素分辨率为13.7 nm。基于图像的孔隙定量仅在三个详细图上进行;小于2 × 2像素的孔隙被排除在孔隙统计之外,得到的等效孔径最小可量化孔径为~ 30 nm (Klaver et al. 2012;Houben et al. 2013;Mathia et al. 2019)。
孔隙分割采用Ilastik 1.3.3post3版本的像素分类工作流程(Shi et al. 2023)。用斐济分析了分段孔掩膜的尺寸和几何分布,sem可见孔隙度大于30 nm的实际分辨率。毛孔面膜已经用手稍微修正了裂缝。
粒度估计
由于晶界重叠,无法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分割,因此对50个最大颗粒的等效直径进行了人工估计。测量是在覆盖大面积的总览地图C1上完成的。采用检测到的最大晶粒(?max)和50个最大晶粒的算术平均值(?max50)作为半定量粒度参数。
正常压实趋势
在以往的许多研究中,正常压实趋势忽略了异常孔隙压力的影响,建立了主要机械压实带泥岩的孔隙度和古埋藏模型(Athy 1930;Baldwin et al. 1985;Drews et al. 2018;Ewy et al. 2020)。考虑到孔隙度与渗透率或驱油压力之间经常存在的直接关系(Yang and Aplin 2007,2010),正常压实趋势曲线也可以作为缺乏岩心直接信息的地区的密封质量预测工具。但是,需要对每个流域的一般趋势进行理想的校准。为了测试其作为驱替压力和最大烃柱高度模型的普遍适用性,在只假设毛细管驱替的情况下,将Yang和Aplin(1998、2004、2007、2010)得出的压实度与孔隙度/渗透率趋势与MICP实验测量的驱替压力和XRD测量的粘土矿物含量进行比较。请注意,原始模型使用粘土含量作为粘土大小颗粒的比例,而本研究使用XRD分析中的粘土矿物含量来显示测量数据。Yang和Aplin(1998,2004,2007, 2010)之后,计算给定粘土含量和给定埋深泥岩的位移压力和HCH的必要步骤如下。在第一步,孔隙度是根据土力学的经典有效应力原理计算的(例如,Terzaghi 1943;Skempton 1969;Burland 1990):
(2) (3)
式中为孔隙率,为孔隙比,为0.1 MPa有效应力下的孔隙比,为孔隙比与竖向有效应力自然对数线性关系的斜率。输入参数和基于假定粘土含量,由孔隙比与垂直有效应力之间的经验关系得出(Yang and Aplin 2004):
(4) (5)
遵循粘土的定义,即直径< 2μm的颗粒的质量分数(Yang和Aplin 2004)。
利用孔隙度与粘土含量的经验关系,可以推导出垂向渗透率:
(6)
其中为层理垂直渗透率。
应用Yang and Aplin(1998)的孔喉模型(图4a),利用Yang and Aplin(2007)建立的计算孔隙度与渗透率的关系,可以计算出平均孔喉半径:
(7) (8) (9) (10)
式中为孔的最大半径与其喉道半径之比,假设一个样品的所有孔都是相等的。为相对于层理方向的平均孔隙排列角。
图4

a Yang和Aplin(1998)假设的孔隙形状。R为孔体最宽半径,R为孔喉半径,L为最宽半径到孔喉R的长度,为成线角。(改编自Yang and Aplin 2007)。b平均孔喉半径(rmean)与位移半径(rdisp)。利用平均孔喉半径与位移半径的相关性(R2=0.93)将Young和Aplin模型的平均半径转化为位移半径
最大烃柱高度估计
Yang和Aplin模型建立了平均孔喉半径的压实趋势。然而,为了计算HCH,需要将平均孔喉半径(rmean)转换为位移半径(rdisp)。这是通过应用从本研究的测量数据得出的以下对数相关性来完成的:
(11)
由实测毛细管压力曲线得出(图4b)。然后,通过将浮力压力与孔隙的毛细管进入压力相等,利用该位移半径计算出理论最大烃柱高度(HCH):
(12)
式中为流体的界面张力(0.035 N/m),为样品的润湿角(0°),为烃密度(0.807 g/cm3),为水密度(1.06 g/cm3), g为重力常数(9.81 m/s2) (Schowalter 1979;Yang and Aplin 2010)。必须注意的是,理论烃柱高度反映的是纯粹的静态毛细管密封行为,而忽略了动态影响以及密封非均质性或不连续性。因此,在本数据集中,计算值大于1500m HCH的情况经常出现,这显然表明实际密封能力被高估了。
对于仅使用BIB-SEM测量的样品,HCH的计算采用本研究中ΦSEM与HCH相关性的回归线:
(13)
Eltra / rock-e瓦尔
使用Eltra Helios分析仪对粉末状岩石样品进行了两次碳和硫测量。测定了经磷酸处理去除无机碳(如碳酸盐)后的总硫(S)、总碳(C)和总有机碳(TOC)。样品用“Rock-eval 6”仪器(Vinci Technologies)进行热解。通过测量S1和S2峰[mgHC/岩石],计算出生产指数[PI=S1/(S1 + S2)] (espitali
et al. 1977)。S1对岩石中存在的游离烃敏感,S2表示热解过程中生成的烃。生产指数代表了岩石中存在的总有机质产生的碳氢化合物的数量。随着温度的升高和深度的增加,会产生更多的碳氢化合物,因此预计深度会增加。考虑到样品的一次源电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主要使用S1和PI来鉴定样品中的烃染色量。S2值< 0.25 mgHC/岩石(4个样品)的Tmax和S1值由于测量偏差明显,被排除在解释之外。
摘要
介绍
地质背景
样本和方法
结果
讨论
结论
数据可用性
参考文献
致谢
作者信息
道德声明
补充信息
搜索
导航
#####
总体矿物学、He-pycnometry、MICP、BIB-SEM和总体地球化学数据见附录表2、3、4和5。
通过XRD分析(图5和图6)定量了以下主要矿物相:云母群矿物(18-37 wt%)、石英(15-35 wt%)、绿泥石(10-24 wt%)、白云石(6 - 21 wt%)和方解石(3-18 wt%)。此外,在部分样品中还检测到微量的斜长石(3-11 wt%)、可膨胀粘土矿物(0-10 wt%)、石膏(0-5 wt%)、钾长石(0-6 wt%)、黄铁矿(0-10 wt%)和菱铁矿(0-3 wt%)。
图5

巴登尼亚样品的整体矿物学分析。样本根据其深度排列(顶部=最浅)。结果以wt%表示。主要物相:云母群矿物、石英绿泥石、白云石、方解石。微量斜长石、消耗性粘土矿物、石膏、钾长石、黄铁矿和菱铁矿均有检出。与其他地层相比,巴登期样品中方解石含量多于白云石,斜长石含量较少。(Qz石英、Pl斜长石、Kfs k长石、Cal方解石、Dol白云石、Py黄铁矿、Sd菱铁矿、Chl绿泥石、ECM可膨胀粘土矿物、Gy石膏)
图6

萨尔马提亚(a)和潘诺尼亚(b)样品的大量矿物学分析。样品按其深度排列(顶部=最浅)。结果以wt%表示。主要物相:云母群矿物、石英绿泥石、白云石、方解石。其中斜长石、可膨胀粘土矿物、石膏、钾长石、黄铁矿和菱铁矿均有微量检出。潘诺尼期样品中粘土矿物含量一般略高,但样品深度与粘土矿物含量之间没有相关性。(Qz石英、Pl斜长石、Kfs k长石、Cal方解石、Dol白云石、Py黄铁矿、Sd菱铁矿、Chl绿泥石、ECM可膨胀粘土矿物、Gy石膏)
在整体矿物学上只观察到微小的地层差异;与萨尔马尼亚和潘诺尼亚样品相比,巴登尼亚样品往往含有更多的方解石和更少的斜长石。此外,潘诺尼亚期样品中块状粘土矿物略丰富,但未见粘土矿物深度变化趋势(图5、图6)。
校正后的干样容重值范围为1.87-2.61 g/cm3,而校正后的ΦMICP值范围为3.3 - 26.7 vol.%,反映了较宽的采样深度间隔。MICP孔隙度值比He密度法得出的孔隙度值更低,其范围为4.7 ~ 31.2 vol.%(图7a, b;补充材料表3)。MICP仅限于> ~ 3nm的孔喉,而在He-pycnometry的情况下为1.2 nm (Freitag et al. 2022),这导致观察到的可检测孔隙度的系统性变化。ΦMICP和ΦHe随深度的变化呈递减趋势,两种方法的孔隙度值分别为:较浅的潘诺尼亚期孔隙度值最高,最深的巴登尼亚期孔隙度值最低。ΦHe和ΦMICP的值具有良好的相关性(R2 ~ 0.96;图7c)表明,尽管所调查样品的渗透率较低,但毛细管压力数据是可靠的,与砂岩等储层型岩石相比,需要更仔细地进行检查(Busch and aman - hildenbrand 2013;Houben et al. 2014;Klaver et al. 2017)。位移半径范围为0.0043 ~ 0.2135μm,深度呈递减趋势,与ΦMICP相当(图7d)。潘诺尼亚样品的位移半径变异性最大(0.0048 ~ 0.2135μm),而萨尔马提亚和巴登尼亚样品的位移半径一般分别< 0.05μm和0.02μm。平均孔喉半径(rmean)范围为0.0048 ~ 0.138μm。驱替压力(pdisp.)在3 ~ 172mpa之间,而突破处饱和度(Vdisp.)在36 ~ 57%之间。潘诺尼亚浅层样品显示出更广泛的孔隙度散射,而在两个孔隙度数据集中,可以看到一个明确的深度趋势,萨尔马西亚和巴登尼亚样品(图7a, b)。只有少数异常值被观察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沉积学特征或胶结模式变化的结果。样品51_HOH-K18_753为强方解石胶结,因此在其深度位置表现出非常低的孔隙度。样品56_SPA14_1405是在与目标泥岩夹层的细砂层段中错误采集的。其位移孔喉半径明显较大(补充资料表3),证实了其粗粒性。深度> 2000 m的样品64_SPA8_2275和49_HOH1_3195的粉砂含量相对较高,可能导致机械压实效果较差。
图7

a总孔隙度值由He-pycnometry与深度标绘(注意,样品是根据地层颜色编码的)。b总孔隙度值由MICP与深度绘制。c不同孔隙度方法的相关性。对于该样本集,这三种方法具有很好的可比性,尽管ΦHe值显示系统地向更高的孔隙度转变,而ΦSEM值系统地更低。d根据毛细管压力曲线随深度绘制的估计位移半径。请注意,位移半径轴为对数尺度。一般情况下,位移半径随深度的增加而减小。一个浅层潘诺尼亚期样本没有遵循这一总体趋势,它达到了非常低的位移半径。e总孔隙度值由BIB-SEM随深度绘制。f BIB-SEM平均孔径与驱替半径半对数图,相关性较弱
基于图像的ΦSEM值在1.18和18.21%之间变化,与ΦHe和ΦMICP相比,这要低得多,这是由于给定映射工作流的实际分辨率限制为30 nm(补充资料表4)。然而,ΦSEM与ΦMICP和ΦHe具有很强的相关性,R2值分别为0.83和0.81(图7c),并且具有相似的孔隙度-深度趋势(图7a, b,e).剔除细砂岩样本56_SPA14_1405使ΦSEM与ΦHe和ΦMICP的相关性R2增大至0.90。
BIB-SEM提供了使用直接从分段孔隙截面中获得的几何参数来描述孔隙形状的机会。从BIB-SEM图中分割的中位孔径范围为54至77 nm,与深度无关(图7f)。由MICP测定的位移半径与BIB-SEM平均截面孔径呈中等趋势(R2 ~ 0.60;图8)。分段孔隙的平均长径比(2.73 ~ 5.14)呈现深度增加的趋势(图8b),而与粘土矿物体积无关(图8c)。平均孔隙圆度(0.45 ~ 0.70)呈极弱的深度递减趋势,与粘土矿物总量无相关性(图8d、e)。
图8

BIB-SEM平均孔径与驱替半径的半对数图,相关性较弱。b平均长宽比(AR)与深度。随着深度的增加,AR值有轻微的上升趋势。c平均AR与TCM。较高的AR值与黏土矿物含量的增加有轻微的相关性,但黏土矿物含量与深度无关。d平均孔隙圆度与深度。随着深度的增加,孔隙形状变得更加复杂。e平均圆度vs TCM。f平均晶粒尺寸与深度的关系。孔径和粒度都与深度无关。这表明所提出的深度趋势不受地质变化的影响
半定量的粒度参数?max和?max50分别在26 ~ 330μm和14 ~ 59μm之间,与深度没有相关性,也没有根据地层层段的系统移位(图8f)。根据BIB-SEM概览图,大多数样品都是基质支撑的,只有一个浅层样品(51_HOH-K18_753;图9)此外,仅在最深的样品中观察到少量方解石胶结。然而,这些样品仍然遵循整体孔隙度-深度趋势(图7a、b、e)。
图9

样品的BIB-SEM图像不符合一般孔隙度深度趋势。样品51_HOH-K18_753在其深度位置(755 m, 6.51 vol. % ΦHe)显示出非常低的孔隙度值。该图像显示孔隙结构具有强烈的碳酸盐胶结作用,导致孔隙度值较低。胶结的详细图像显示在(e)中(红色矩形标记了呈现元素的位置)。b Sample_56_SPA14_1405在其深度位置具有异常高的孔隙度(1406.5 m, 24.64 vol. % ΦHe)。微观结构图像证实,这不是分析偏差,而是因为细砂岩被错误取样。c和d具有较粗粒度的样品,导致较高的预期孔隙率。e (a)中红色矩形的细节显示了孔隙结构的强碳酸盐胶结作用
计算出的最大HCH值在132 ~ 6612 m之间变化,其深度趋势是在最浅的潘诺尼亚层段最小,在最深的巴登尼亚层段最大(图10a)。毛细管压力曲线的平均孔喉半径和计算的HCH值与数学压实模型计算的趋势总体拟合较好(图10b、c)。从图10b、c中可以看出,XRD的体积粘土矿物含量与模拟的黏土矿物含量线不一致。请注意,粘土矿物可以大于粘土品位,并且没有给出这两个参数的一般相关性。然而,黏土矿物含量的变化趋势似乎能更好地反映在黏土矿物含量较高的浅层样品(ΦMICP > 10-15 vol.%)和较弱的压实作用中,而低孔隙度样品的估计密封能力对黏土矿物含量没有敏感性。通过ΦSEM绘制的HCH值与R2值相关,R2值为0.80(图10d)。
图10

a估计最大HCH随深度的变化。观察到的HCH深度趋势表明,大多数调查样品的压实作用是正常的(注意,样品是根据地层学的颜色编码的)。b平均孔喉半径与ΦMICP的对比c HCH与ΦMICP的对比。(b)和(c)中的虚线是根据Yang和Aplin 1998,2004,2007,2010的模型计算的。d ΦSEM vs HCH。请注意,之所以选择潜在的相关性,是因为HCH的计算只考虑半径和孔隙度(半径的平方)。e总粘土矿物含量与HCH的比值。f基于图像的粒度表示绘制的与HCH的。HCH与总粘土矿物含量无关,也与sem图像得出的粒度平均值无关。BIB-SEM HCH=由MICP计算得到的BIB-SEM平均孔径与驱替半径的相关性计算出的油气柱高度
样本51_HOH-K18_753是一个例外,尽管其深度较浅,但HCH值极高;这可能是由于粘土基质的体积粘土矿物含量极高和方解石胶结作用广泛造成的(图9a, e)。该样品的ΦMICP为1.18 vol.%,平均位移半径为0.0048μm,在样品集中属于最低值。
测量的TOC含量几乎全部< 1 wt%,除了Pannonian样品27_BO8_900,其TOC含量为2.5 wt%。背景信号校正后,S1和S2峰的绝对值较低(S1: 0.03-0.46 mgHC/ rock;S2: 0.2-1.3 mgHC/岩石),表明可忽略的主要来源潜力和长期储存期间潜在的额外挥发性损失。然而,信号仍然足够强,可以比较S1和PI的相对变化(补充资料表5)。S1值与深度的关系表明,深度趋势略有相反,这在样本的巴登尼亚子集中尤为明显(图11a)。PI值在0.07 ~ 0.45之间,呈现出较弱的深度递减趋势(图11b)。与计算的HCH值相比,S1和PI的变化趋势更清晰。HCH越低的样品S1和PI值越高,反之亦然(图11c, d)。
图11

a随深度绘制的岩石评估S1。虽然信号强度较低,但可以看到相反的深度趋势。b Rock-eval PI随深度的变化趋势相反。由于明显的测量问题,样品22_BO157_1653.5的结果没有显示在图中。S1值仅在S2 > 0.25时显示。(请注意,样品根据地层颜色进行了编码)c岩石评价S1与HCH的对比显示两个参数的弱相关性d岩石评价生产指数(PI)与HCH的对比显示两个参数的弱相关性。BIB-SEM HCH=利用BIB-SEM平均孔径与MICP驱替半径的相关性计算出的油气柱高度
下载原文档: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s00531-023-02331-4.pdf
为您推荐:
- 一项新研究表明,夜猫子有更多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患糖尿病的风险要高出72% 2025-08-31
- PS5和PC上的新《地狱潜水员2》对玩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25-08-31
- 《罗宾汉》新剧开拍,现代版重新演绎主角 2025-08-31
- 维也纳盆地区域泥岩压实趋势:顶封评价及其隆升史意义 2025-08-31
- 美国老兵涉嫌在推翻马杜罗的未遂政变中走私武器被起诉 2025-08-31
- 在最近一次轰动的阿森纳进球后,大卫·拉亚将自己提升为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 2025-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