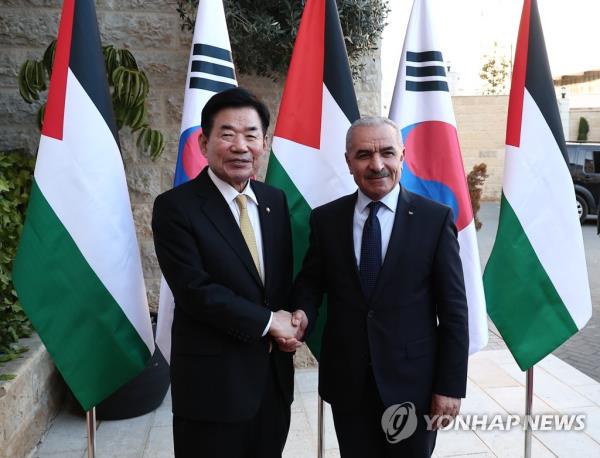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经常用陈词滥调来谈论爱。我们吹嘘它的重要性,并投入时间、金钱和艺术来研究它的每一寸情感广度,试图达成理解。
然而,我们中很少有人真正谈论爱情重心的世俗性。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大学实习时遇到了约翰·桑丁(John Sandeen);我们去约会;世界变得不可磨灭地饱和,就像一张过度曝光的夏日照片。对我来说,爱上他就像决定要呼吸一样自然。你呼吸,因为你不能没有它;我嫁给他是因为我无法想象没有他的生活。
我嫁给他是意料之中的事。1991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他的死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约翰在1989年的感恩节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毒。他让我离开他。我说没有。
这个决定来得很容易,因为这就是爱的作用:它把一个人面临的最困难的决定简化成一句话。“没有。”我当然不会离开他。当然他无论如何都会死。我当然很爱他,所以留下来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我很幸运,因为我的母亲是一名临终关怀护士。死亡和濒死就像出生和结婚一样是随意的话题,它总是在我的脑海里若隐若现,这种对我们最终目的地的意识。那时候,像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我以一种随随便便的超然态度对待它,以为自己永远不必面对它。
直到很久以后,当我见到约翰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正面临死亡。这个故事最大的悲剧之一是,在他被确诊之前,艾滋病毒就已经在破坏他的身体。在当时,艾滋病就像被判了死刑,大家都知道,每个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的人都会在两年内死亡。就其毒性和副作用以及疗效而言,现有的治疗方法并不比完全拒绝治疗好多少。
照顾一个将死之人的生活出乎意料地平淡,但这只是因为我必须强压下我所感受到的最强烈的情感——愤怒、悲伤和爱——才能让我的家庭正常运转。我们是一对年轻夫妇,有一个孩子,汉娜,还有约翰前妻生的两个儿子,艾滋病毒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
每天,我醒来,给汉娜做早餐,照顾她的孩子。我会和约翰的临终关怀护理人员讨论一下他的需求,然后去上班,然后回家喂汉娜。我麻木了。我恋爱了。我是一个母亲,一个照顾者,一个有丈夫的寡妇。
有一天,一位临终关怀的工作人员给他带来了一张床,我知道我会看着他在床上死去。
约翰有时也会过得很好——他头脑清醒的时候——在那些日子里,他能说一两句话,如果我们幸运的话,也许还能在床上坐起来。在那些日子里,他会试着弹钢琴或弹吉他,或者想听音乐,他心爱的巴赫或尼尔·杨。当音乐在我们家停止时,我意识到他的核心已经消失了。但他的身体还在那里——他的呼吸很浅,痛苦的线条蚀刻在他的脸上。
有一天,当笼罩在他断断续续的句子上的狂热阴霾消散到足以让他清楚地说话时,他让我杀了他。
你必须结束这种痛苦,”他低声说。“我再也受不了了。”
我当时27岁,这句话悬在空气中,像静止而可怕的湿气。我知道他想要什么——清醒地死去,知道他已经告诉了我、汉娜和他的儿子们他临终前需要说的话。他想带着健康时的尊严死去;他想知道我们知道他爱我们爱到不会让我们眼睁睁看着他死去。我不能合法地把钱给他。

对约翰来说,最基本的任务都变成了与自己的身体进行痛苦的能量谈判。他再也抱不住汉娜了。他的钢琴连一个和弦都弹不出来。一段时间后,他不能照顾自己。
剥夺这些最基本的尊严,是一种耻辱。对约翰来说,直到今天他仍然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这是毁灭性的。他本来就很结实,但艾滋病却把他蹂躏得皮包骨。他的大脑,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吸引我的东西,开始瓦解,他只能说短句。
约翰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去死。艾滋病夺走了他的这一切,法律也禁止他在死亡时寻求医疗援助。但他给我留下了最后一份礼物。
在约翰病情恶化的初期,我们一起计划我的下一步——申请社会工作研究生课程。他不安分,而且有一种奇怪的强势,这和他不一样,他坚持要阅读我的论文,帮我准备申请工作。最终,我意识到这是他在放下这个世界之前要完成的最后任务之一。他于1993年12月去世;我的研究生申请截止日期是1994年1月。
两年半后,我成为了一名社会工作者,他临终遗愿的幽灵驱使着我,我需要给别人我不能给他的东西。这就是我如何参与到有尊严的死亡,一个国家组织,与像约翰这样的人一起争取临终医疗援助法律,我现在是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我一生致力于创造一种环境,让垂死的人可以决定自己的死亡,让他们在健康的时候保留自己的尊严。
20年后的今天,约翰去世的爱荷华州仍然没有“有尊严地死亡”的法律,但我们已经在10个州成功地通过了有尊严地死亡的权利。今年,在纽约、马萨诸塞州、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州,州议会有机会通过他们自己的关于有尊严死亡的法律。
为每个人有尊严地死去的权利而战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决定向我仍然爱着的男人的生命致敬——1991年我拒绝离开的男人。在一个艾滋病不再是死刑判决的世界里,仍然有绝症打断爱的生命历程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爱需要一种坚持的方式——这就是我传递爱的方式。
你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吗你想在赫芬顿邮报上看到什么故事?找出我们在这里要找什么,然后给我们发个广告。
为您推荐:
-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朝鲜去年接受了23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2025-07-13
- 主要的黑人保守组织谴责佛罗里达州的新教育政策 2025-07-13
- 起亚汽车将于上半年在国内推出EV9 SUV 2025-07-13
- Coupang推出豪华美容购物服务Rocket luxury 2025-07-13
- 现代劳恩斯首席设计师被选为2023年世界汽车年度人物 2025-07-13
- 今天,11月20日,西隆蒂尔比赛结果直播:西隆蒂尔、晨蒂尔、居外蒂尔、卡纳帕拉蒂尔、夜蒂尔等比赛第一和第二轮的中奖号码 2025-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