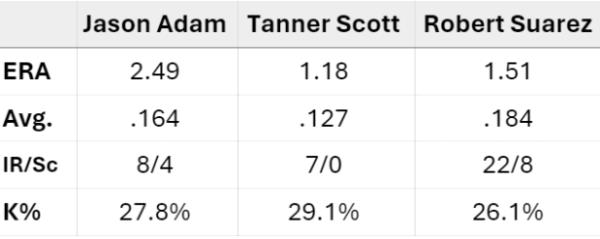
当代艺术家雨果·克劳斯韦特(Hugo Crosthwaite)的职业生涯一直在颠覆传统,其中包括他在梅萨学院美术馆(Mesa College Art Gallery)的最新展览。两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从事壁画表演,在他工作/表演的同时,他还穿上了一套服装,并有机会让参观者(或观众)与他互动。
“白立方的破裂:Hugo Crosthwaite的装置”展示了这位出生于蒂华纳的具象艺术家的绘画、定格动画和素描作品,这些作品围绕着他在家乡看到的美和个性(展览将持续到9月12日)。这次展览的另一个元素是在他的作品中对美墨边境的叙述,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呈现,而不是在画廊空间中典型的体验。在画廊内建造了一个12英尺高的白色立方体,重现了目前大多数画廊的设计,这些画廊都是用白色立方体结构建造的,有一个全景窗口,让人们可以在他的现场绘画会议期间观看克罗斯韦特的工作。这次展览的目的是打破传统的展览体验,以及他的定格动画电影《提安娜,我的爱》(Tia Juana, Mi Amor)和他的一系列描绘提华纳人民及其生活的纸上作品,题为《提华纳的颜色》(Linea a Tijuacolor)。周一下午5点至7点,克罗斯韦特和展览策展人兼设计师斯玛达·萨姆森(Smadar Samson)将在画廊进行一场特别的观看和对话。在这里,他们每个人都花了一些时间谈论挑战传统和惯例的愿望,以及它可以如何赋予权力。(为了篇幅和清晰度,这些对话经过了编辑。)
问:这个展览是如何形成的?你为什么想这么做?
Crosthwaite:策展人Smadar Samson找我做这个项目。她有一个项目,在一个画廊空间里展示一个白色的立方体,她希望有人能在这个立方体里表演。她看到了我的作品,看到我把这些壁画的概念作为一种表演,这是我过去20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我在2014年的厄瓜多尔昆卡双年展上做过这样的项目,我也在纽约做过,作为我作品的一部分,在那里我把这些壁画作为一种表演而不仅仅是壁画。我进入一个空间,在两到三周的时间里,在没有任何预先计划或任何准备草图的情况下,在墙上即兴创作图像。只是我带着画笔和一小罐颜料进入空间,在空间中即兴创作图像。她认为这对她在立方体内展示艺术的想法来说是完美的,尤其是艺术品会冲出立方体的想法,会从立方体中脱离出来因为Smadar Samson关于立方体的概念是关于艺术是如何,在过去的,我不知道,50年里,在立方体的概念中呈现出来的。画廊就像这个白色的立方体,以及艺术品是如何在这种贫瘠的环境中装饰或呈现的。她希望有人能摆脱这种束缚,有人能在这个立方体里做艺术,但又能摆脱这个空间非常贫瘠和精英主义的想法。它非常适合我,当我进入这个空间的时候,我把这个定格动画投影在立方体内的一面墙上。然后,在立方体的墙壁上,我即兴创作了提华纳市,这是我心目中的家的假想世界。我在立方体外面画了一点,呈现出这个想法,是的,它打破了立方体它打破了这个立方体内部消毒的想法。
问:画廊对这次展览的描述是“一部分是给他的城市的情书,一部分是对传统画廊体验的挑战”。首先,你如何描述传统的画廊体验?《白立方的破裂》在哪些方面偏离了传统的经验?
克罗斯韦特:我认为策展人斯迈达尔引用了这个立方体的概念,认为它是一个非常精英的空间,所以我们如何看待在白色空间、白色画廊中进行艺术展示,这是一个无菌的地方,它将单个艺术品隔离在这个白色空间中。这就像我们展示艺术的一个惯例,但是这个装置“白立方的破裂”打破了这个惯例,因为它是一个在立方体内的表演。我在这个空间里画这些壁画,它是对公众开放的,所以人们可以进来,他们看着我工作,他们和我互动,他们看到了在现场创作的东西。然后,当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我穿着这件衬衫,背面有字母写着“雨果,Rótulos”,意思是“标识画家”。我穿着这件衬衫在这个空间里,所以观众不知道我是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工匠,或者是艺术家雇来做这幅壁画的人。即使在那里,艺术家在画廊里的概念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我是一个角色,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你不知道我是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被雇来做这件事的工匠因为我的衬衫上写着“本地标识画家”,就像被雇来的人一样。甚至艺术家的概念都是悬而未决的,然后我在空间里即兴创作这幅壁画,在展览结束时,这些壁画都会被摧毁。即使是艺术是不朽的这个想法,我们试图赋予壁画这种不朽,特别是传统的壁画,比如米开朗基罗或迭戈·里维拉,墨西哥的壁画。壁画一直被认为是不朽的理念。我们画这些画是为了永远留在那里,让世世代代的人欣赏。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这个空间里即兴创作了这幅壁画,但在展览结束时,它将被重新粉刷,然后拆除并摧毁。人们看到我在这里工作是一种短暂的体验,但这是一种表演。在这方面,它打破了艺术不朽的传统。
参孙:为了理解这次展览的背景,我需要谈一谈白立方画廊起源的想法。世界上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白色的立方体画廊。大多数当代艺术画廊都有相同的建筑设计,我们称之为“传统设计”,这是100多年前发展起来的。这是对19世纪欧洲沙龙的一种批判性回应,当时,在画廊里,厚重的框架杰作被密集地挂在不同的高度,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有不同的厚重框架。新的观念是,艺术品需要呼吸的空间,以便为自己说话。抽象艺术的出现和影响力的包豪斯风格建筑在20世纪初(包豪斯建筑有巨大影响的设计白立方画廊),抓住的原则在欧洲和美国都是中性的,白墙,没有装饰,最好是没有窗户,创建一个纯,极简主义的空虚的艺术作品可以没有任何干扰与外界的联系。一个没有社会或政治参考的永恒空间;这是最初的想法。
批评者在70年代开始对这个想法表示反对。爱尔兰评论家和艺术家布莱恩·奥多尔蒂的一篇非常著名的评论文章。他将白色立方体规则的严格程度与建造中世纪教堂的规则进行了比较。评论家们不仅质疑这个空间的纯粹性,还质疑它宣称这种永恒状态的意识形态概念,把画廊变成了一个“地狱”。因此,在白色立方体画廊里展示的任何东西都被提升了一种神圣的光环,就像在一个神圣的地方,就像在一个教堂里。在这样的不确定状态下,其他的声音令人窒息,许多游客感到疏远。随后,在70年代,在非传统的空间,比如仓库、阁楼和工厂,甚至在大自然中,开始了许多精彩的、具有煽动性和创新性的展览。与此同时,艺术家团体开始挑战艺术界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掩盖了他们推动艺术界的政治和经济依赖。这些批判性的观点和展览在今天仍在继续,但当艺术的内容变得不那么孤立,更有效地对社会评论时,白立方画廊的设计和框架仍然是世界各地展示当代艺术的默认模式。这确实是一个强大的设计范例,所以我邀请雨果来打破这个范例,真的,在我们眼前。
问:你是如何想到这个概念的?你和雨果都谈了些什么?
萨姆森:首先,我想说的是,雨果的政治作品是对边境生活文化的有力见证,他的作品打破了任何结构框架。我是说,他在墙上作画,在栅栏上作画,在柱子上作画,在陶瓷雕塑上作画,任何能见证他令人回味的故事的东西。他的想法是,在过去的一周里,雨果会一丝不苟地画出他心爱的家乡蒂华纳的建筑景观,首先是在白色的立方体结构内部。他的即兴创作流畅,他的即兴绘画与蒂华纳临时住所和建筑的建造动态完美共鸣,这些建筑不断波动,以回应边境短暂的生活。随着每一波新的移民、移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到来,一个新的房间被添加到另一个摇摇欲坠的小屋,这个小屋建立在另一个临时房屋的另一个扩建上,以此类推。在立方体内部的视频投影中,我们可以听到孤独的建筑工人的敲击声,伴随着来自不同州的乐队的声音,他们都带着欢乐和传统的乐器聚集在一起。就像这座城市本身一样,这幅画超越了它的边界,落在白色立方体的原始、干净的外墙上。所以,我们所经历的是内部变成了外部,外部可以窥视内部。
问:你能谈谈展览中展出的作品吗?
克罗斯韦特:我在这次展览中有两件作品,一个是立方体,这个立方体的概念在画廊的中间,我展示了我制作的定格动画的投影,题为“Tia Juana, Mi Amor”,意思是“我的爱”。它在玩弄这种想法,有点像《巴黎,我爱你》或《纽约,我爱你》等电影的即兴表演。这是一部关于提华纳的电影,提华纳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城市。这就像一封情书,献给了提华纳这座城市的混乱、建筑和即兴美学。这是立方体内部的主要部分,它是这个三分钟定格动画的投影,在一个循环中。然后,在过去的两周里,我一直在立方体周围即兴创作这些壁画。在立方体的外面,我正在展示另一件名为“Línea a Tijuacolor”的作品,这是一系列的画作,它们都排成一条线,在画廊的另一个角落。提华纳市也是这样一个城市,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地理边界所界定。然后,它展示了提华纳市的人们,色彩和城市景观在这条非常独特的线内,打破了画廊另一端的角落。
这件作品长30英寸,宽40英尺,横跨画廊的一角。这是对立方体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回应,即立方体内所有的图像都是黑白的。
问:你想通过这条线条,这个彩色的边框,而不是立方体所代表的黑白,来传达什么?
克罗斯韦特:这有点像对它的视觉反应,因为当我第一次进入这个空间时,最初它只是这个立方体的装置和我的壁画表演,但后来,作为立方体的一部分,我们决定建造这个全景窗口,就像这条线一样,也进入立方体的一个角落。从美学的角度来说,我想做一些能呼应立方体里全景窗户的东西,但是在画廊的另一边。同样,对立方体的回应是,这个作品将是彩色的,而不是立方体内部发生的事情,都是黑白的。这些是我决定做这个“Línea a Tijuacolor”的主要概念,以回应立方体中发生的事情。它还涉及到蒂华纳的概念,我个人对如何定义蒂华纳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提华纳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和墨西哥的地理分界线界定的。就连我的名字,克罗斯韦特,都是19世纪40年代在加州定居的名字,甚至在这条边界线出现之前。即使对我来说,在我个人的经历中,我的家庭是一个被分隔开的家庭,因为在美墨战争期间,这条地理界线突然出现了。还有,“你的身份是什么?”我是第一个来这里的,从来没有要求成为墨西哥人或美国人。
然后,它运用了这条图像线的概念这条图像线非常局限于这条地理线。一切都在这条非常严格的界线内进行,整个蒂华纳市的混乱和活力,人们,街道,标牌等等。这一切都被这条清晰的线所限制。它也明确地引用了蒂华纳这个城市在很大程度上被这条边界所定义,特别是在9/11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它变得军事化了。我记得这个城市被描述为一波打破了非常明显的边界的人。蒂华纳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条地理线界定的。
在立方体内部,也有这个窗口反映了那条线以及图像是如何脱离那条线,脱离立方体的。这个想法,是的,我们可以尝试放置地理线和地点,但人们会移动。这有点像我们不能呆在一个地方的基本权利,不是吗?我们喜欢四处迁徙,寻找更好的去处。不管你怎么努力,你都不可能阻止人们的流动。这也是这条线所代表的东西之一,人们移动的移民概念。美国人自己也来自不同的地方,从欧洲和其他地方,来到这个国家;这里有基本的行动自由,但在蒂华纳和圣地亚哥,他们试图阻止这种行动。这有点像徒劳的实验,徒劳的努力。
问:你能谈谈现场绘画环节吗?
克罗斯韦特:基本上,我在立方体内做的壁画参考了我在立方体内呈现的定格动画。整部电影,以及所有这些壁画的整体概念,都是这个电影标题的想法,就像一个特定城市的“我爱你”电影。他们在评论这些伟大的城市,但这部电影是我对这些电影的诠释,我在纪念提华纳。从来没有人认为提华纳是一个伟大的、普遍的、不朽的城市。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一个非常贫穷的城市,一个非常混乱的城市。这是一个由边界界定的城市。这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城市,现在,谋杀率非常高。所有这些都是你不会想要放进一部纪念这座伟大城市的电影里的。
在影片中,你看到的是定格动画,我正在即兴描绘提华纳市——不同的建筑,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它们是如何建造的。在这个故事中,它提到了提华纳正在发生的中产阶级化。它质疑了家的概念,对我来说,提华纳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家。在影片的最后,展示了土坯结构的建筑,参考了提华纳城市出现之前这里的建筑,当库梅耶人在这里定居并建造土坯结构的时候。这就像一封写给这座城市建筑的情书,就像一篇关于蒂华纳的建筑散文。当然,这幅壁画是关于这一切的,关于提华纳这座城市,门窗的结构,标牌,垃圾场和轮胎。它遍布整个空间,就像视频中的图像刚刚涌向墙壁,现在它也涌向立方体外面。
问:从你的角度来看,挑战这些传统的艺术展示方式如何赋予你作为艺术家的力量,为艺术的叙事服务,并为他人的声音提供力量?
克罗斯韦特:问题是,我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艺术家。我一生都在画画。绘画一直是我创作的主要动力,所以这里展示的绘画实践是对这种绘画实践的庆祝,通过定格动画,通过壁画的表演,到墙上的图像线上所显示的东西。所有这些练习都归结于我的速写本,这是我每天从生活中画画的练习——画人物,画环境,创造意象。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通过练习,我有了一种技能,就像一个音乐家。你每天练习五个小时钢琴,十年后你掌握了这门乐器,所以我掌握了绘画,我掌握了创造意象,不是吗?在某种程度上,这与艺术家作为概念大师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人有想法,另一个人建立它们。在这里,我只是一个有动力用我自己的手,用我的技能创造图像的人,就像钢琴家或小提琴家一样,他们掌握了一种乐器,你所听到的是个人的触摸和技术,这是一个人经过多年的练习和练习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你在这里看到的,在这个特别的艺术作品中,你看到的是一个画画的人,他喜欢画画,正在从他们来自的城市蒂华纳创造意象,并通过我的绘画实践重塑这个城市。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就像是对技术的庆祝,对简单的绘画行为的庆祝。在那里,我处理来自我所在城市的概念——移民的概念,城市暴力的概念,这种跨文化化和生活在边境的问题——但这一切都是通过艺术家,通过技术,通过绘画实践来过滤的。
出版:
为您推荐:
- 在受到查尔斯国王的冷落后,哈里王子似乎陷入了沉思,没有任何魅力 2025-05-23
- DRT服务日益普及 2025-05-23
- Commsignia和博世联手提高弱势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2025-05-23
- 蒂华纳艺术家Hugo Crosthwaite在Mesa学院画廊的新展览中打破了框框 2025-05-22
-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领取遗产福利的人将于下个月收到DWP的信件 2025-05-22
- 乔丹·勒夫明显的腿部受伤让包装工队感到紧张 2025-05-22


